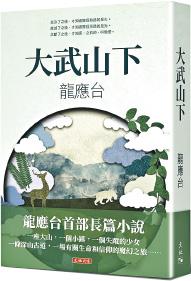

26 7 2020
讀了這篇文章,好想讀龍應台首部長篇小說《大武山下》,她
”推薦讀者帶著小說去旅行,按圖索驥走一趟文學行腳,也希望這本小說,對身處於這個令人惶惑的時代的讀者,會帶來療癒的作用。”
【明報專訊】2017年,龍應台為了照顧失智的母親,毅然拋下一切,到屏東大武山腳定居。至今,她於這片土地已經生活了三年多,她形容這段日子是「豐收期」,對她起了強大的療癒作用,讓她重新思索語言的作用、人與大自然的關係,乃至何謂生命的本質。
今年,龍應台出版首部長篇小說《大武山下》,以孩童般無止盡的好奇、田野調查者追根究柢的執著,刻劃出大武山的世界。小說講述一名沒有名氣的作家,大半生浪蕩天涯,對生命的惶惑一直無解,當她回到闊別五十年的鄉村,卻與一名十四歲的神秘少女相遇,展開了一段光影交織的魔幻旅程。
龍應台過往擁有多重身分,除了任教於台灣、香港、美國等多所大學外,也曾出任文化部部長一職,她說:「在政府裏頭工作,常常覺得力不從心,對民主政治的發展,也覺得不盡理想。我離開都市的時候,是帶著懷疑和不確定感的,這也是時代的特徵。然而這片大山大地卻療癒了我不安的心。我也希望這本小說,對身處於這個令人惶惑的時代的讀者,會帶來療癒的作用。」原本只是單純地為著陪伴失智的母親,走畢人生「最後一哩路」,卻意外讓她回到大海和森林,重新和大自然連結。
「身處於大都會的人們,很容易萌生『我的世界就是中心』的觀念,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從所謂的『中心』走進『邊緣』,從『邊緣』眺望,你會發現邊緣的視野更深沉,更開闊。在大山腳下生活的人,他們的面貌、色彩、生命的力量,是如此的鮮明。」三年來,她穿梭於鳳梨田、香蕉園之間,深入大武山認識原住民部落。三年來獵人和果農變成了她的老師。她親身體驗氣候變遷對農作的影響,也了解過絕不浪漫的農人生活。譬如連連大雨,芒果農擔心的是,「雨水太多,芒果容易得炭疽病,幼果枯萎,熟果變黑……」
虛構的人物 真實的精神
龍應台在小說後記中,寫下這番話:「書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虛構的,唯一真實的是人物的精神,所以不必對號入座。只是下回走進任何一個鄉間小鎮,你知道,馬路上走著的、市場裏蹲著的、田裏頭跪著的,斗笠和包頭布蒙著的,皮膚黑到你分不出眉目的,每一個人,都有他生命的輕和重、痛和快,情感負荷的低迴和動盪。」同樣地,對於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、蟲魚鳥獸,龍應台也是帶著一顆匍匐在地的謙卑和感恩之心去書寫。綜觀全書,讀者不難發現,小說裏所有對動物、植物的稱謂都是用上「他」,而不是「它」,這並非誤植,而是作者刻意為之,目的是表達出「人,不在動物、植物之上」的信息。
在〈十四歲可以思索的問題〉一章中,主人公有一日義務給小鎮的國中生上語文課。作者把十四歲的孩子形容成一隻「人頭羊腳的中間過渡動物」,聽起來引人發噱的比喻,其實也不無道理,書中是這樣描述的:「他不是小孩也不是大人,他的女生像男生,男生像女生。他前一分鐘憂鬱地坐在那裏說出讓大人嚇得睡不著的人生警句,譬如,『你知道嗎,我覺得人生是不值得活的』——父母驚嚇得半夜秘密討論是不是要找兒童心理醫生,下一分鐘他已經在操場上追打嬉鬧,像一隻體力充沛、無法控制的小獸。」
認真看待十四歲的讀者
「我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,心裏就有一位十四歲的讀者。」龍應台認為在華人社會的傳統思想裏,傾向小看了少年人。 「我們把他們看『小』了,幾乎把他們看成兒童。其實十四歲的少年,可以像大人一樣,思考人生最深邃的問題,偏偏大人們仍舊把他們當小孩看。在這小說裏,我想要認真對待十四歲的人。他們會天真胡鬧討論什麼是『渣男』,但他們絕對也有能力思考人生根本的問題。」故事中,作家把試卷發給學生,要求學生們用半小時寫下答案。龍應台笑著說:「我真的試過為這裏的國中生上作文課,小說出現的問題也是真實的問題。」
當中有些古怪的問題,竟換來令人失笑的答案,如「兔子一定比烏龜早抵達終點嗎?」,有人答「不一定,說不定兔子半路碰到獵人。」;問到「把全世界的鐘表都拿走了,還有時間這個東西嗎?時間是什麼?」,得到的回應是「我阿嫲用她繡學號的布尺量我的身高,總不能說,丟掉尺,我的身體就不在了吧」。上述答案當然是屬於小說虛構的部分,但龍應台就建議中學老師不妨試試拿這些問題去問學生,「十三、十四歲『羊頭人身』的小孩們,什麼都有可能,我們千萬不要用考試制度、填鴨教學,把他們縮小成一個方塊。」
屏東位於台灣的最南端,一個由閩、客、原住民混居的五萬人小鎮,龍應台打趣地說,每次走過小鎮的街道,一路上都要跟人打招呼。無論是經過花店、蛋餅攤子,還是飯湯店,東主都會熱情地跟你聊天。小說中,龍應台精準細緻地捕捉了小鎮居民善良、單純的性格特質,雖然這些角色是虛構的,但人物的精神卻無比真實。
其中一位是主人公的房東,他的祖上留下很多田產,由於他常常抱著皮包去收租,因此得了一個「員外」的暱稱。一般地主的形像都是愛財如命,員外卻是個眼睛總是瞇瞇著笑的好人。舉例說,有一日,一位老農走來,羞澀地對員外說,想再續租兩年,問他可不可以不要加價。員外乾脆地說:「可以。」老農不知道該不說什麼感激的話,只從腳踏車的籃子裏拿出一袋沉沉的番薯,交給員外,然後靦腆地說:「紅心的,很甜,又軟,可以拿給你老母吃。」
員外又會用不同的名字寫信給坐牢的人,陪伴他們渡過人生的難關,例如以「蕉妹」的身分寫信給立榮,「她」在信中寫到:「你說你剛剛換到一個有小窗的房間了,雖然窗子很小,很高,而且永遠鎖死的,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個角的藍天。我好開心。只要你看得夠久,總會看到一隻鳥剛好飛過那格小窗。說不定,就是那隻吃了我蓮霧的小鳥。」蕉妹足足寫了八年信給立榮,為的只是給予他一個活下去的希望。
《大武山下》從香港大嶼山拉開序幕,再聚焦台灣屏東大武山下,最後回到大嶼山,這個佈局的安排別出心栽,龍應台說:「大嶼山代表的是香港,小說從大嶼山開始和結束,這不是偶然的,在香港住了九年,香港在我心中有一個柔軟的地方。」由於今年疫情來襲,除了書展延期外,因應隔離政策,她也無法前來香港與讀者見面。但是,她仍然有一番說話,想送給香港讀者:「我很想告訴我香港的讀者,人的生命是有很多個面向的,如果其中一個面向碰到了阻礙,打結了,你可以繼續灌溉其他的面向,讓它成長。」
對於較年輕的讀者,她說:「假設我們的生命有九十年,前二十五年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,當然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,但它也是一個很小的部分。所以,如果在前二十五年,你恰好撞見了時代的創傷,那並不代表你的生命就因此要停頓在這個創傷之中,你還是要去想,我之後的二十五年,要怎麼樣才不辜負自己的生命。」身處於一個擁擠的城市,龍應台提醒我們,儘管生活多忙碌,也要不時停下腳步,盤點自己的生命處境,相信能獲得新的體會。
打開小說,首先會看到一張作者手繪的地圖:「在書寫時,左轉有天后宮、右轉有茄苳樹、東邊是毛豆田、西邊是香蕉園;員外住南邊、小鬼住北邊、製冰廠在前面、文具店在後面……轉來轉去自己都昏了頭。畫了地圖,小鎮就清晰而立體了。」
龍應台推薦讀者帶著小說去旅行,按圖索驥走一趟文學行腳,她不忘調皮地說:「不過,先警告你們,裏面有真有假的啊!」沿著大武山自北往南蜿蜒的縣道一八五,經過三地門、內埔鄉、碼家鄉、萬巒鄉、新埤鄉……坐在小鬼和作家待過的,那個30.5km的地方,究竟能看到什麼景象呢?答案留待讀者自行去探險見證。
文//柯美君
圖//受訪者提供
編輯//陳志暘
fb﹕http://www.facebook.com/SundayMingpao
「我很想告訴我香港的讀者,人的生命是有很多個面向的,如果其中一個面向碰到了阻礙,打結了,你可以繼續灌溉其他的面向,讓它成長。」
(台湾作家龍應台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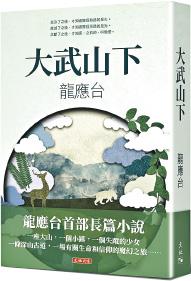
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